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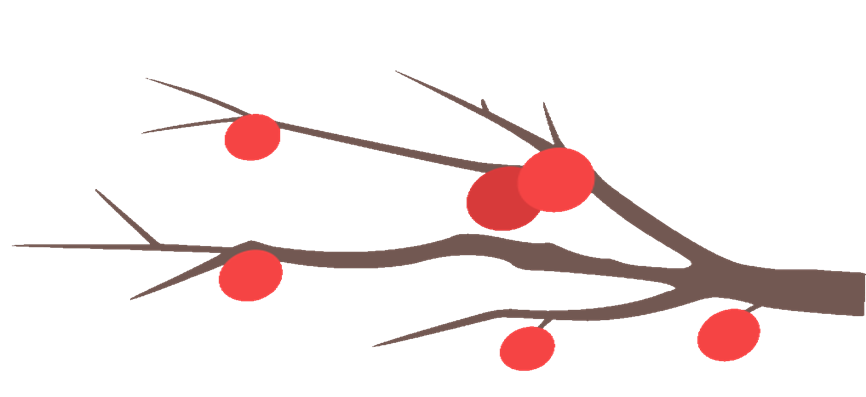
汉字性质综论
李运富 张素凤
(本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摘要:关于汉字的性质,国内外专家学者长期争论不休,其实并没有大的矛盾,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因为各自针对的材料不同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如果把古今汉字当作一个总体,并且从字形、字构和字用三个角度来全面认识汉字的属性,可以把汉字的性质概括为:汉字是用表意构件兼及示音和记号构件组构单字以记录汉语语素和音节的平面方块型符号系统。
关键词:汉字;性质;字形;字构;字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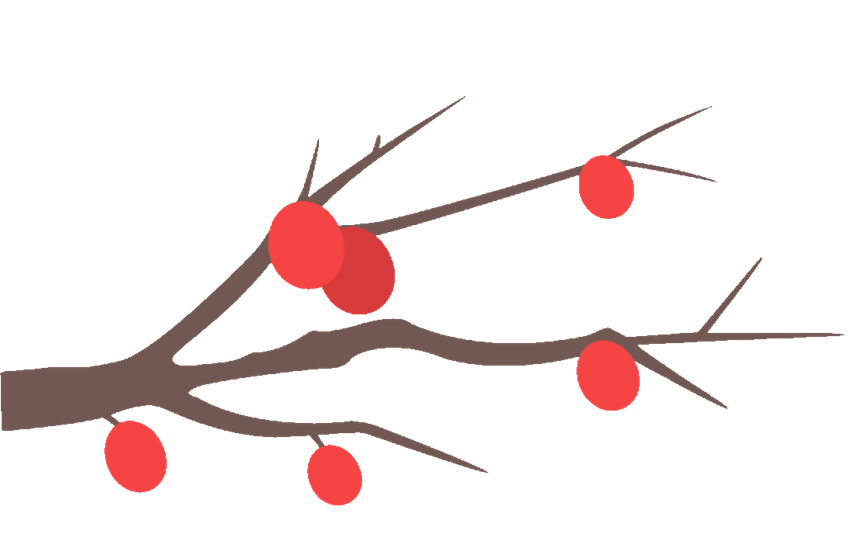
一、汉字性质异说述评
如何对汉字进行定性,是学术界近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诸如“表意文字”“象形文字”“意音文字”“表音文字”“音节文字”“语素文字”“表词文字”“语素音节文字”“意符音符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表词文字—语素文字”“图画文字—假借文字—形音文字”等等,不一而足,都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汉字性质的不同表述;同一名称,如“表意文字”,含义也多种多样。这些对汉字性质问题的五花八门的看法,往往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令人无所适从。
其实,种种关于汉字性质的表述,有的大同小异,措辞不同而已;有的内容虽异,所指不同,也并不一定矛盾,因为它们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时代说的,各自都反映了汉字的部分属性,所以不能简单地是此非彼。下面把一些主要的说法归纳为不同的角度,以便分析各种说法的具体涵义和实际所指,从中可以看出各自的分歧表现在哪里,是怎么引起的,这有助于认识争议的实质,弥合分歧。
(一)从汉字的表达功能角度定性
1.表意(义)文字说
对汉字性质最早做出明确论断的是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瑞士语言学家德·索绪尔。他说:“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1]显然,索绪尔把汉字定性为表意文字,是因为汉字通过它所记录的语言单位——词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意义发生关系。这一看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例如詹鄞鑫、孙钧锡等就赞同这个观点。①
这种“表意文字”指的是文字表达词或语素的意义。还有一种观点,虽然也把汉字定性为“表意文字”,但他们所说的“表意文字”指字形直接表达事物或概念的意义,与索绪尔等所说的表意文字的含义不同。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可以看作这一观点的代表,他这样表述汉字的“表意文字”性质:“在中国,一如在埃及,文字不过是一种程式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系统。就是说,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的词再去表达概念。这就意味着,书面语言是独立于口头语言的各种变化之外的。”②可见帕默尔定性的“表意文字”指可以不通过语言直接表示概念的文字。和帕默尔观点相似的有袁晓园、申小龙、毕可生等。③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是文字的共性,也是文字区别于图画的本质特征,汉字作为文字大家庭中的一员,也必然以记录语言为前提,即必须通过语言表示意义,即使是早期的象形文字能够让人产生图景联想,也只有落实到联想人的语言上,才能确切地感悟到字形所显示的具体意义,因此认为汉字可以不通过语言直接表达事物或概念的观点是错误的,它混淆了文字与图画的本质区别。至于说汉字表达了汉语的词义或语素义,因而属“表意文字”,这当然是对的,但从符号系统来说,世界上哪种文字不表达它所记录的语言的词义或语素义?不能表达语言的意义,那要文字干什么?何况,就个体汉字的使用来说,有时也并不一定表达意义,例如“沙发”中的“沙”和“发”,所以绝对地说汉字是“表意文字”也不周全。
2.表音文字说
姚孝遂坚决反对古代汉字是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的说法,他认为古代汉字“并不是通过它的符号形体本身来表达概念,而是通过这些文字所代表的语音来表达概念。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其形体本身与所要表达的概念之间,并无任何直接的关系”。因此,古汉字“从它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只能是表音文字,而不是表意文字(或象形文字)。”[2]后来,姚孝遂进一步指出,文字发展阶段和文字符号的构形原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必须严格区分。他说:“文字的发展阶段,是就文字符号的功能和作用所到达的程度来说的;文字的构形原则,是就文字符号的来源来说的。”“就甲骨文字的整个体系来说,就它的发展阶段来说,就它的根本功能和作用来说,它的每一个符号都有固定的读音,完全是属于表音文字的体系,已经发展到了表音文字阶段。其根本功能不是通过这些符号形象本身来表达概念的,把它说成表意文字是错误的。”[3]
显然,姚孝遂所说的“表音文字”也是从表达功能角度立论的,其根据是“每一个符号都有固定的读音”,要通过“所代表的语音来表达概念”。汉字能表音固然是真理,但正如刘宁生所说,这样做的“结果是:英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日语的书写符号系统、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都成了一类。由此得出一个最简单的公式:一切文字=‘表音文字’”。[4]所以,从表达功能角度把汉字定性为“表音文字”的做法,跟从表达角度把汉字定性为“表意文字”一样,虽然也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什么文字不能“表音”,但通过记录语言而表达语言的“音”和“意(义)”是所有文字的共性,这样为汉字定性对于区别世界不同文字体系之间的差别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二)从汉字的记录单位角度定性
1.表词文字说
布龙菲尔德作为欧美现代语言学的权威学者,主张汉字为表词文字。他说:“从表面看来,词显然是首先用符号表现在文字里的语言单位,用一个符号代表口语里的每个词,这样的文字体系就是所谓表意文字”。但是他接着又说表意文字“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名称,文字的重要特点恰恰就是,字并不是代表实际世界的特征‘观念’,而是代表写字人的语言的特征,所以不如叫作表词文字或言词文字。”[5]王伯熙对这一观点的表述更加明白,他说:“从文字符号所记录的语言单位这个方面来看,汉字应该属于表词文字,因为它的每个独立字符基本上都是音义结合体,即形、音、义的统一体,是词的书面符号。”[6]
2.表词·音节文字说
《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版“文字”(writing)条把文字发展历史阶段列为表格,将世界文字发展阶段分为非文字阶段、前文字阶段、真正的文字阶段。而真正的文字阶段又分为三个文字阶段:①表词·音节文字阶段,②音节文字阶段,③字母文字阶段。汉字被归入表词·音节文字阶段。
3.语素(或词素)文字说
最早提出汉字为词素文字的是赵元任。他说:“用文字来写语言,可以取语言里头各等不同尺寸的单位来写。……在世界上通行的能写全部语言的文字当中,所用的单位最大的文字,不是写句、写短语的,是拿文字一个单位,写一个词素,例如我们单独写一个‘毒’的字形,来写‘毒’这个词素……以上是讲用一个文字单位写一个词素,中国文字是一个典型的最重要的例子……他跟世界多数其他文字的不同,不是标义标音的不同,乃是所标的语言单位的尺寸不同。”[7]吕叔湘、朱德熙、李荣等也都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④
4.音节文字说
张志公说:“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在汉语里,没有用某个音素表示某一种或某几种语法范畴的形态标志这种现象(英语books,looks,my brothers,letters里的[s]音素)。因此,汉语在实际使用中只需要表示音节(包括单元音或复元音形成的音节)的符号,不需要只表示音素的符号。汉字是音节文字而不是音素文字,与汉语的非形态性相适应。”[8]显然,张先生称汉字为“音节文字”,是从汉字与记录语言的音节单位的对应关系来说的。
5.语素音节文字说或音节语素文字说
这种说法有两个含义,一个指除记录语素外,有时还记录不是语素的纯音节。叶蜚声、徐通锵所说的大概就属于这个含义:“汉字由于种种原因还维持着意音文字的格局。它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即每一个汉字基本上记录语言中的一个单音语素;少数语素不止一个音节,只能用几个字表示,但每个字记录一个音节,如‘玻’‘璃’‘彷’‘徨’等。”[9]
另一个含义指汉字所记录的语素同时也是一个音节,所以叫音节—语素文字。尹斌庸的表述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汉字基本上代表一个语素。从语音上来说,一个汉字又表示一个音节。因此,综合上述理由,我们建议把汉字定名为音节—语素文字,或简称为语素文字。这一名称较好反映了汉字的本质特点。”[10]
记录语言是文字的共性,但不同文字“可以取语言里头各等不同尺寸的单位来写”,这就有了差异,就可以体现不同文字的区别性特征,因而从记录语言的单位角度来揭示汉字的性质应该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三)从汉字的结构理据角度定性
1.象形文字说
20世纪初,孙诒让在《名原》中提到汉字发展的三个阶段:“其初制必如今所传巴比伦、埃及古石刻文,画成其物,全如作绘”,是“原始象形字”;其后发展为如一般甲骨文那样经过简化省略的“省变象形字”;最后发展为篆书那样截然有别于图画的“后定象形字”。[11]显然,孙诒让把古汉字都叫做“象形字”。此外,云中、吴玉章和英国的历史学家韦尔斯也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⑤
2.注音文字说
唐兰指出:“中国的文字是特殊的,在一切进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时期,她却独自应用一种本来含有义符的注音文字”[12]。他所说的“注音”不同于拼音,应该指在义符基础上加注声符以表音的现象,这是以形声字的构造为根据的。
3.表意文字说
王宁提出:“汉字是表意文字,早期的汉字是因义而构形的,也就是说,汉字依据它所记录的汉语语素的意义来构形,所以词义和据词而造的字形在汉字里是统一的。这一点,在小篆以前的古文字阶段表现得更为直接、明显。”[13]这是从汉字构形方面来说明表意文字的,即汉字的形体结构跟所记语素的意义有内在联系,因而叫表意文字。⑥
4.意音文字(音义文字)说
徐银来较早地把汉字称为音义文字,他说:“故在今日中国文字在其作用上而言,其一代表本字之读音也,谓之为音符可也;其一代表本字之意义也,谓之为义符可也。在古谓之形声,在今谓之音义,此音义之文字,为吾国文字之特性。或谓中国文字为形系之文字,吾宁谓之为音义系文字”。⑦周有光也认为汉字就是意音文字,并指出“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文字的组织原则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字在有记录的三千多年中间始终是意音制度的文字,古今的不同只是在形声字的数量和符号体式的变化上。”[14]
5.意符音符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两阶段说
裘锡圭认为“一种文字的性质就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所以他根据构成汉字的字符特点,对汉字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表述:“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严格说应该称为借音符)的一种文字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主要是义符)、音符和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隶书的形成可以看作这种演变完成的标志)。如果一定要为这两个阶段的汉字安上名称的话,前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像有些文字学者那样把它简称为意音文字;后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考虑到后一个阶段的汉字里的记号几乎都由意符和音符变来,以及大部分字仍然由意符、音符构成等情况,也可以称这个阶段的汉字为后期意符音符文字或后期意音文字。”[15]
6.图画文字—表音文字—形音文字三阶段说
刘又辛认为一切文字符号表示词语的基本方法可以归纳为三种:表形法、表音法和表形兼表音的方法。象形字、会意字和指事字都是表形字。单用表形法造字的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属于人类文字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表形字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文字发展阶段,属于人类文字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表音文字主要指假借字,商周时代的古汉字属于这一阶段;在此以后,世界文字的发展却走向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道路沿着表音文字的方向继续发展,于是表形文字逐渐被淘汰,逐渐演变成纯粹表音的音节文字或字母文字。这是世界大多数文字所走的道路。另一条道路,保留了一部分表形字和借音字,但主流却向表形兼表音的形声字方向发展。这是汉字所走的道路,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16]
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当然具有内部的结构,不同文字系统的内部结构元素和结构规律是有差异的,差异往往反映属性的不同,所以从内部结构上分析汉字的属性也是科学合理的。
(四)从汉字的区别同音词角度定性
表意文字说
王力指出:“汉字有字形、字音和字义。这三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但是汉字只是表意文字,不是表音文字,因为同音的字并不一定同形。”[17]显然,王力是从汉字能区别同音语素的角度称汉字为表意文字的。曹先擢在肯定汉字是语素文字的同时,也认为汉字能区分同音词和同音语素,因而可以从这个角度称汉字为表意文字。⑧
这是从汉字的别词作用来证明汉字为表意文字,看似有理,其实它与汉字的性质无关。因为汉字区别同音词的作用体现为字与字之间的一种局部关系,而不是普遍属性。作为属性的区别性则是所有文字的共性,任何文字符号都是能够相互区别的,这种区别性跟王、曹所说的区分同音词不是一回事。即使就别词作用而言,汉字也不只是用意义来区分同音词,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同义词和同类词是靠读音不同来区别的,还有同形字有时也要靠读音来区别,例如同义符的形声字就是以声别义的,多音字也是以音别形别义的。另一方面,汉字并不能区分汉语中的所有同音词,例如花朵的“花”和花费的“花”、连词的“以”和介词的“以”等等,它们同音而异义,属于不同的词,字形上却没有区别。再说汉字中还有大量同音同义而字形上却有差别的异体字,这是用汉字的表意区别功能解释不了的。可见汉字的形音义关系是复杂的,同音异词而异字(形)者只是其中的一种,表意具有别词作用,表音有时也有别词作用,所以不能把同音词的用字不同抽象为汉字的一种“区别”性质,也不能用同音词的意义不同来证明汉字的“表意”性质。
(五)从多角度为汉字定性
有的表述涉及两个角度。如梁东汉说:“分类要看这些符号所表达的是怎样一个语言单位。是表达整个的词,抑或是表达词的一个音节或音素。”“符号表达‘个别的完整的词或者它的独立的部分’的文字体系叫做表意文字体系。”[18]司玉英说:“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包括词文字和语素文字。古代汉字是词文字,现代汉字是语素文字”[19]。
这是从汉字记录的语言单位和汉字表达的内容两个角度来立说的,既说汉字是“表词文字”“语素文字”,又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如果汉字是“表词文字”或“语素文字”,就不能把汉字局限为“表意文字”,因为“表词”“表语素”必然包括“义”和“音”两个方面,语言中的“词”或“词素”(语素)是音义结合体,不可分割,世界上没有只表意(义)而不表音的文字。分开来说,“表词文字”也好,“语素文字”也好,“表意文字”也好,在一定的条件和范围内都是正确的,但不宜说“表意文字”就是“表词文字”或“语素文字”,也不宜说“表意文字”包括“词文字”和“语素文字”,它们之间属于不同的角度,没有对应的等同关系或包含关系,所以上面的表述及其他类似的表述是欠严密的。
也有从记录单位和结构理据两个角度说的。裘锡圭指出:“语素-音节文字跟意符音符文字或意符音符记号文字,是从不同的角度给汉字起的两种名称。这两种名称可以共存。”[15]
有的表述涉及三个角度。如周有光提出汉字有“三相”,应该从三个角度综合起来为汉字定性。从符形角度(或叫符位相)说,汉字属于字符文字;从语音角度(或语段相)说,汉字属于语词音节文字;从表达法角度(或表达相)说,汉字属于意音文字。综合三相,可以将汉字定性为“字符+语词和音节+意音”文字。[20]杨润陆也从三个不同角度分别为汉字定性:从记录语言的方法看,汉字属于意音文字;从记录语言单位的大小看,古代汉字属于表词文字,现代汉字属于语素文字或语素音节文字;从记录语言的文字字符看,汉字属于意符音符记号文字。[21]
从多个角度为汉字定性的做法值得我们重视,但选择哪些角度不是随意的,周有光和杨润陆选择的三个角度值得借鉴,但还可以斟酌完善,我们的意见将在下文中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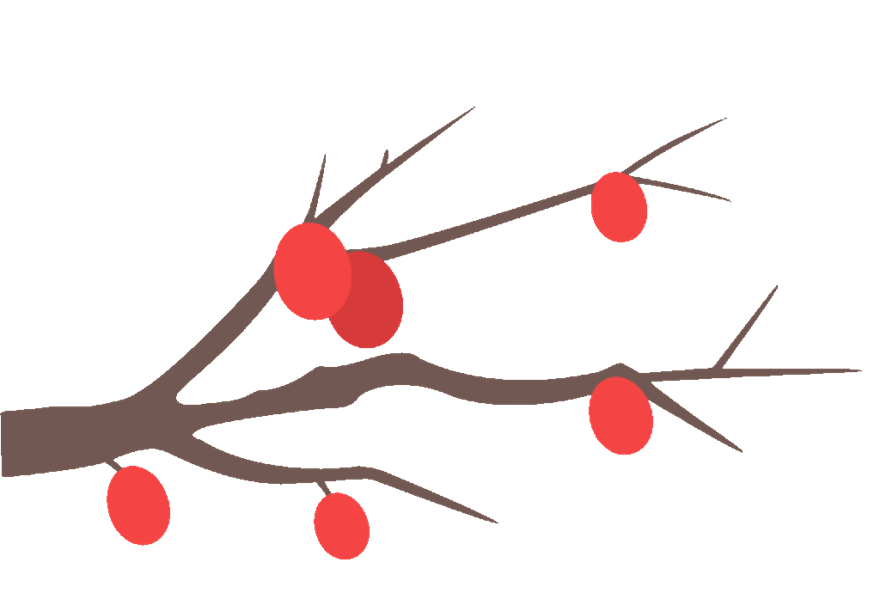
二、我们对汉字性质问题的认识
以上列举了关于汉字性质的多种说法,有的同名异实,有的异名同实,我们按立说的出发点归纳为几个不同的角度。除了“区分同音词”不属于性质问题外,其他角度都是能够揭示汉字的某些属性的。就是说,在一定条件和一定范围内,那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各自从不同的角度立说,同一角度也有不同的表述,往往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甚至只认为自己的对,别人的一定不对,因而长期争论不休,这对正确认识和掌握汉字的性质无疑是不利的。
我们认为,要统一对汉字性质的认识,必须首先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汉字的性质是就全体成员而言,还是就部分材料而言。上述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些是针对汉字的部分材料而言的,对象不同,认识自然不同。例如有人说汉字是“象形文字”,就是针对“西周”以前的文字而言;有人说汉字是“表意文字”也主要体现在“早期”或“小篆”以前;有人根据“甲骨文字体系”或“大多数古文字”把汉字定性为“表音文字”;有人说古代汉字是“表词文字”,现代汉字是表“语素文字”;所谓“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等等,也认为汉字的性质具有阶段的不同。根据不同的时期和特定的材料来分析汉字的不同特点是可以的,根据不同的特点来确定性质的不同表述,只要说明对象也是科学的。但人们往往把从部分材料归纳出的特点当作全体汉字的性质,一般说汉字的性质是什么什么的时候,不再针对具体的材料,因而误解和争议也就在对象不明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地发生了。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争论,我们认为在分析具体材料的时候,尽可以根据材料说话,但在一般表述汉字的性质时,最好把“汉字”当作一个整体看待,所谓“性质”要能够涵盖古今所有汉字,这样大家才可能说到一起。
其实,“汉字”的性质是可以概括表述的,因为就总体而言,古今汉字的属性只有数量的差异而并无类型的不同。从已经发现的最早成体系的甲骨文字发展至今,大约有了将近四千年的历史,这期间无论是个体字符还是整体字系都发生过多次变化,但这些变化只导致汉字某些属性的量变,而汉字的根本属性并没有质的不同,所以我们认为古今汉字的性质可以有个统一的概括性的表述,没有必要分别加以界定。例如说古代汉字是表词文字、现代汉字是语素文字,其实古代的词变成现代的语素是属于语言问题,就字来说它所记录的音义体并没有变化,何况词与语素是可以同时共存、相互转化的,古代的单音节词也未尝就不可以看作语素(成词语素),现代的单字也可以记录一个词,而且古今汉字都还能记录不是词或语素的音节。就是说,汉字在每个时期所能记录的语言单位类型是一样的,都包括词、语素、音节三种成分,只是记录各种成分的比率因时而异(古代记录词的机会多一些,现代记录语素和纯音节的机会多一些)罢了。再如说前期为意符音符文字而后期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其实前期也有记号,例如甲骨文用ㄓ表示“有”,用![]() 表示“入”,用丨表示“十”,战国文字有许多没有音义功能的变异构件和赘加构件,甚至已经能够自觉使用简化符号“二”来取代别的构件了,这些不都是没有音义功能的记号吗?只是汉字隶变以后特别是现代汉字,其中的记号更多一些而已。所以就总体而言,汉字的性质应该是可以概括和统一起来的。
表示“入”,用丨表示“十”,战国文字有许多没有音义功能的变异构件和赘加构件,甚至已经能够自觉使用简化符号“二”来取代别的构件了,这些不都是没有音义功能的记号吗?只是汉字隶变以后特别是现代汉字,其中的记号更多一些而已。所以就总体而言,汉字的性质应该是可以概括和统一起来的。
第二,汉字的性质是单方面的还是多方面的。上述关于汉字性质的各种不同说法,主要是由于观察角度不同造成的。立足点不同,对汉字的属性认识就可能不同,这原是十分正常的。问题在于,有的学者只承认自己所站的角度看到的才是汉字的“性质”,而别人从另一角度看到的就不是汉字的“性质”,于是争议就在所难免了。例如上文引到裘锡圭的话说:“语素—音节文字跟意符音符文字或意符音符记号文字,是从不同的角度给汉字起的两种名称。这两种名称可以共存。”[15]但在同一书中又说:“讨论汉字性质的时候,如果不把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跟文字本身所使用的字符的性质明确区分开来,就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进而强调汉字的性质“是由这种文字所使用的符号的性质决定的”,“只有根据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才能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型”。[15]这似乎有点矛盾,实际上裘锡圭把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看作了不同事物的不同性质,而只承认“字符”的性质才是“汉字”的性质。裘氏所说的“字符”就是构成文字的符号,也就是构件。构件的特点当然能反映汉字的属性,但为什么“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性质”就不是汉字的属性呢?为什么“只有根据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才能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呢?似乎很难说通。实际上“字符特点”的分析通常是专家们的爱好,对一般使用文字的人来说,他们所了解的恐怕首先是文字的外形和文字作为语言的符号的记录功能,他们主要是根据文字的外形和功能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所以不顾“文字”的其它方面而只把“字符特点”当作区分不同性质文字的根据是有失偏颇的。同样偏颇的是强调另外某一个方面,如潘钧指出:给文字定性的唯一标准是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不同,“语素文字”是汉字唯一的本质属性,其他属性都是非本质的,是由“语素文字”这一本质属性决定的。[22]什么是“本质属性”?有区别性特征、能将一事物跟另一事物区别开来的属性,就是本质属性。那么,汉字区别于其它文字的属性仅仅是记录单位的不同吗?“语素”是汉字唯一的区别性特征吗?显然不是,否则裘锡圭肯定不会同意,因为他觉得“字符的特点”也就是构件的功能才是决定汉字性质的区别性特征呢!又如郑振峰说:“根据汉字的功能,根据汉字所记录的语言单位来判定汉字的性质,不可能准确、全面地揭示出汉字的一般特征,显示出汉字和其他文字体系的本质区别。”而“应该通过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即构形原则,从整个文字构形系统演变规律角度来判定文字的性质”。[23]而司玉英又坚决反对郑的观点,认为“文字的性质取决于文字体系中单个符号与语言单位的对应关系。表音文字的单个符号对应的语言单位是音素或音节,表意文字的单个符号对应的语言单位是词或语素。这是由创制文字时人们对语言的切分方式决定的。”[19]这种分歧跟上举裘锡圭与潘钧二人的不同看法如出一辙,都简单否定了多角度的兼容性而过于强调了单角度的排他性。
其实,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而各个角度的认识结果可能并不一致,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单角度的考察往往只能揭示事物性质的某个方面,而难以反映事物性质的全貌,只有把各个角度的不同属性综合起来,才能获得对事物的全面而客观的认识,才能真正把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出来。因此,为了更准确的描述事物和区分事物,我们在确定某一事物性质的时候不妨多选择几个观察点。汉字的性质也应该多方面地考察,如果把各方面的考察结果综合起来,就有希望获得汉字性质的“准确、全面”的认识,就能避免各执一端的分歧争议。
那么,应该选择哪些角度来考察汉字的性质呢?我们在前文“多角度定性”一项里提到了周有光、杨润陆的三角度定性法,值得重视。周有光认为可从符位相、语段相、表达相三个方面来观察,把汉字定性为“字符+语词和音节+意音”文字。他的“符位相”指的是文字的外形,“语段相”相当于文字的记录单位,“表达相”大概是指形体的表达功能,这三个角度的选择是比较科学的,但有关术语过于生涩,“字符”“意音”这样的名称歧义太多,将汉字形体的表达功能归纳为“意音”不够准确,有些具体表述也还值得斟酌。杨润陆认为:从记录语言的方法看,汉字属于意音文字;从记录语言单位的大小看,古代汉字属于表词文字,现代汉字属于语素文字或语素音节文字;从记录语言的文字的字符看,汉字属于意符音符记号文字。所谓“文字的字符”跟裘锡圭的说法一样,是指汉字的组成构件。所以后两项跟周有光的后两项角度大致相同。但第一项“从记录语言的方法看”,“记录方法”属于用字问题,不属于汉字本体的性质问题,因而由此推出的“汉字属于意音文字”的“意音”指汉字记录语言时有的表意,有的表音,有的既表意又表音,实际上跟第三项的“意符”和“音符”很难区分,跟同书所谓文字的共性中的“文字既表音又表意”也交叉重复,不太容易理解和把握。而且杨先生对汉字的性质没有一个总体的归纳,不便指称。
文字的共性是相对于非文字而言的,汉字的个性则是相对于其它文字而言的。我们讲汉字的性质,当然是指汉字的个性,所以选择观察角度应该注意两个原则,一是这个角度必须跟汉字的属性相关,二是这个属性必须带有跟其它文字相区别的特征。在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的各种角度中,第(四)项“区别同音词”角度与汉字的性质无关,首先排除。第(一)项“从汉字的表达功能角度”虽然能反映汉字的属性,但这种属性缺乏区别特征,是所有文字共有的,对汉字来说是非本质的,可以忽略。剩下的第(二)项“记录语言单位”角度和第(三)项“构形理据角度”都是具有区别性特征的,应该作为汉字的性质来概括。另外,汉字的外形实际上也是不同于其它文字的,也应该作为汉字性质的一个方面。总之,汉字具有字形(外部形态)、字构(内部结构)、字用(记录职能)三个不同侧面,因此,我们也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归纳和表述汉字的性质。
(一)汉字外形方面的属性
汉字的外形属性表现为平面方块型。不管是象形意味较浓的早期汉字,还是隶变楷化后的后期汉字,都是方块型而非线型的。书写形式上,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虽然一些字的写法还没有十分规范,但就每个字的外部形态或轮廓来说,已经显示出了呈方块型的特点:为了使每个字大体上能容纳在一个方格里,组成合体字的构件往往采取不同的配置方式,如左右相合、上下相合、内外相合等等。隶书、楷书的字型呈现为十分整齐的方块型,有些构件在不同的位置常常写成不同的形体,如“心”“手”“水”“火”“衣”“示”等字作构件时,位置不同写法就不同,目的就是使整个字能够容纳在一个方格里。总之,汉字外部形态以拼合成字后能写在一个方格里为原则,所以人们常用“方块字”来概括汉字的外形特征。一般谈汉字性质时不提这一点,其实这是人们最容易感觉到的汉字的区别性特征,它明显不同于英文等线型文字系统,线型文字的字母和构件组合在一条直线上(如“workshop”),没有上下、内外等位置的变化,不需要局限在方块内,所以“平面方块型”应该是汉字具有区别特征的本质属性之一。
(二)汉字结构方面的属性
文字的构形单位是构件。任何文字系统都有一批组成单字的构件。英文单字的构件主要起表音作用,有的同时也能表意。例如单字“Work”可以切分出三个直接构件“w+or+k”,三个构件都是纯表音的;而“workshop”可以切分出两个直接构件“work”+“shop”,这两个直接构件是表意的,但同时也是表音的,因为其中包含六个表音的间接构件(w+or+k)+(sh+o+p)。可见,表音是英文构件的主要功能。相对而言,汉字是以表意构件为主的。汉字构件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三种,即表意、示音和区别(通常称为记号)。其中表意性构件包括象形表意、象征表意、义符表意、词语表意、标志表意等细类,示音构件有时也兼表意。这三种功能的构件,就来源而言,是先有表意构件,后有示音构件的,示音构件都由同音的表意字充当,都是借音符;就构字能力而言,表意构件既可以与示音构件组合成字,又能自相组合构字,而示音构件一般只能与表意构件组合成字,而很少自相组合构字;至于区别性记号构件属于理性规定的其实也很少,大都可以认为是表意或示音构件讹变失去原有功能所造成的。可见这三种功能在汉字结构中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大致说来,表意是汉字构形的主体,同时兼用示音构件和区别性记号构件。但如果因为表意是主体就把汉字称为“表意文字”则是不全面的,我们无法置汉字构形中大量的示音构件和记号构件于不顾。至于把汉字称为“象形文字”,那就更缺乏代表性了,象形构件在整个汉字系统中只占少数,可以归入表意构件。还有人把汉字称为“意音文字”或“注音文字”,依据是汉字大都为“形声字”。形声字虽然是汉字构形的主体,但并不是汉字构形的全部,而且随着汉字形体和语言音义的变化,真正的形声结构越来越少,“意音文字”或“注音文字”之称也值得忧虑。至于把古今文字从结构上分为若干个阶段,分别称为“意符音符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或“图画文字”“表音文字”“形音文字”等,其实也只是就主体材料而言,并不能涵盖汉字构形的全部,各阶段间也没有截然的类型区别。作为泛指“汉字”的性质表述,还是笼统一些、全面一些为妥。
(三)汉字职能方面的属性
原始汉语的语素或词项都是单音节的,与之相适应,汉字也是单音节的,一个单音节的汉字正好可以用来记录一个单音节的音义结合体——语素。后来由于音节的衍分和音译外来语,汉语出现了多音节语素,而汉字仍然是单音节的,要完整地记录一个多音节语词或语素,就得同时用多个汉字,这时的每个汉字所记录的仅仅是一个音节而不是语素。因此,从总体来看,汉字只跟汉语的音节对应,而无法跟汉语的词或语素一一对应。所以如果概括地说,汉字的职能就是记录汉语的音节,包括有意义的音节(语素)和无意义的音节(非语素);但如果只说记录音节,容易把记录有意义的音节(语素)这一主要职能掩盖,从而误认为汉字记录的音节都与意义无关,为了避免出现误解,表述时可以把“语素”显示出来,说成“记录语素和音节”。在这一角度上,前面介绍了“表词文字”“表词·音节文字”“语素(词素)文字”“音节文字”“语素音节或音节语素文字”等说法,其中“表词文字”“语素(词素)文字”“表词·音节文字”都难以涵盖汉字职能的全部,“音节文字”说概括性最强,但没有突出汉字记录语素的主要职能,相对来说,还是“语素音节文字”或“音节语素文字”比较符合汉字实际。“记录语素和音节”之所以是汉字的本质属性之一,因为它跟别的文字不同。就英文而论,一个英文单字记录的是一个词,而一个词不等于一个音节,也不等于一个语素,所以英文是真正的“表词文字”[24]。正因为如此,英语只有“词典”没有“字典”,实际上词典就是字典,而汉语编了字典还要编词典,字词根本不是一回事。通常把英文叫作“拼音文字”或“音素文字”,如果从构形理据角度看是可以的,但如果把英文的字母当作文字,进而把英文的“字”跟英语的“音素”对应起来,则是错误的。因为英文的“字母”不等于“文字”⑨。文字的单位是记录语言时能自然分割的单位,英文的字母在词中连写,不是自然分割单位,独立的字母没有固定的音,也没有固定的义,怎么能说是文字呢。我们说英文是“线型文字”,这“线型”也是指“book”这样记录词语的“单字”的外形,而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字母“b”或“o”或“k”。英文中显示音素的是“构件”(如“oo[u]”),而不是“文字”,也不是“字母”。英文的字母跟英语的音素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否则为何还要用国际音标注音?“字母”是书写“文字”的单位,相当于汉字的“笔画”,而不等同“汉字”本身。英语字词统一,每个字必然记录某个词;汉语字词不一致,一个字记录的不一定是词,可能是不成词的语素,也可能是连语素也不够格的音节,但一个汉字必然记录某个音节。所以从记录职能上看,英文才是“词文字”,而汉字应该是“音节文字”。我们说汉字是“音节文字”,主要立足于汉字的共有职能,而不是指汉字的唯一职能。如果汉字只能记录音节,那根本无法区别同音词;或者说如果只为汉语的音节制造字符,那几百个也就够了,何需成千上万!所以说,虽然汉字都能记录音节,但汉字的主要目的是记录汉语的音义结合体——单音节语素(包括单音节语词),这一点在揭示汉字性质时应该有明确的表述。所以我们不把汉字简单地称为“音节文字”,而把它叫做“语素音节文字”。
综上所述,我们对汉字性质的看法可以概括为:汉字是用表意构件兼及示音和记号构件组构单字以记录汉语语素和音节的平面方块型符号系统。相应地,英语文字的性质可以表述为:英文是用具有表音功能或者表音的同时兼具表意功能的构件拼合单字以记录英语单词的线性符号系统。考虑到人们已经习惯了“表意文字”“表音文字”这样简单的分类和称述,为了指称方便,我们也可以分别从外形上把汉字叫做“方块型文字”,以区别于英文等“线型文字”;从构造上把汉字叫做“表意主构文字”,以区别于英文等“表音主构文字”;从记录职能上把汉字叫做“语素音节文字”,以区别于英文等“表词文字”。
注释
① 詹鄞鑫的说法对索绪尔的观点有所阐发,见《20世纪汉字性质问题研究评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孙钧锡的“表意文字”说见《中国汉字学史》,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转引自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14页,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年8月。
③ 他们的论述可分别参阅:袁晓园《汉字的优缺点与语言文字理论的发展》,《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申小龙《汉字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语文建设通讯》1993年12月第12期;毕可生《汉字的社会学研究》,《汉字文化》1993年第2期。
④ 他们的有关论述分别见:朱德熙《汉语语法丛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吕叔湘《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语文近著》(P142),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李荣《汉字的演变与汉字的将来》,《中国语文》1986年第5期。
⑤ 他们的有关论述可参阅:云中《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字学》,《真知学报》2卷6期,1943年;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P3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H.G.Wells《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⑥ 郑振峰对这一观点有进一步的阐发,详见《从汉字构形的发展看汉字的性质》,《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3期。
⑦ 徐银来《中国文字的特性》,《夜光》1卷2期,1931年。转引自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P2),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年8月。
⑧ 详见曹先擢《汉字的表意性和汉字简化》,《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17),语文出版社,1987年。
⑨ 司玉英认为表音文字中的“字母”跟表意文字中的“字”是对等的文字单位,理由是“这是普通文字学确定文字类型的基础和前提”。我们认为普通文字学有一些假设的基础和前提,不能引以为据。而且普通文字学从“字母”与“字”是对等单位出发来划分文字类型,司玉英却又借这样划分的文字类型来证明“字母”与“字”是对等单位,属于循环论证。司说见《关于“字母”和“字”——文字学理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基本问题》,《语言》第1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也谈表意文字与词文字、语素文字的关系——兼与郑振峰先生商榷》,北华大学学报2005年2期。